

我只能说,爱之深思之痛。
耶鲁研究员史蒂芬·罗奇(Stephen Roach)昨天在FT发表文章,“It pains me to say Hong Kong is over”。我就不翻译了,意思大家明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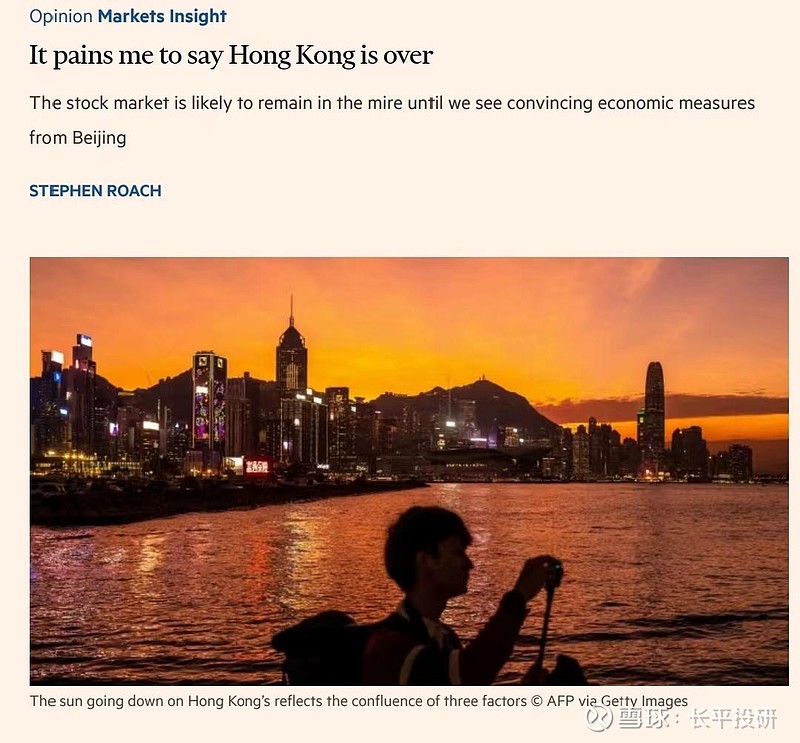
他在文章的结尾处写道:“我永远不会忘记上世纪80年代末第一次到香港的经历。尽管飞机在旧启德机场着陆时出现了令人惊怕的陡降,但我立刻被商界非凡的活力所吸引。当时,香港人既有远见,也有策略。恰好中国经济刚刚开始起飞,而香港正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发展奇迹的主要受益者。一切进展顺利,比任何人预期得都要长。现在一切都结束了。”
香港的变局与中国内地无法切分。罗奇是个知华派,因为多年驻扎香港,他也对大中华区的成长故事倾注了个人感情。在高盛奥尼尔发明“金砖国家”(BRIC)一词时,罗奇作为大摩(Morgan Stanley)首席经济学家和后来的亚洲区主席,是更活跃的亚太经济,特别是Great China的参与者和评论者。
那时,他不仅是“华尔街最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之一”,也被认为是“最懂中国的西方经济学家”。有关中国的重要事项或政策调整,差不多都能听到他较为独特的声音。自2001年以来,除疫情两届外,他几乎每年均受邀参加中国“两会”后的最高规格议事论坛——中国发展高层论坛。

早年我在做财经记者这行时,多次与罗奇在大摩中国的简报会上交流,主题往往是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潜力或风险等。12年前我在耶鲁时,专门到他设在耶鲁管理学院的办公室,与他再谈中国经济的“失衡”(过度依赖投资和出口而忽略消费提升)和“再平衡”。
他在耶鲁开设的课程聚焦亚洲,一门叫“下一个中国”(The Next China),将中国作为实例,讲述经济增长模式如何实现重大转变,即从投资和出口导向型转向国内消费驱动型。另一门叫“日本的教训”(Lessons of Japan)。
很可惜,那时中国经济正以两位数的年率增长,他和其他学者的类似建议似乎并不迫切;待到现在,GDP增速下行至5%左右时,这类建议好似仍非共识并难见有力举措。
近几年,罗奇的兴趣点增加了影响中国经济的地缘政治因素——中美关系。2022年,他转至耶鲁大学法学院蔡中曾中国中心(Paul Tsai China Center,以蔡崇信父亲之名命名),担任高级研究员,这一年,他出版了关于大国关系的专著《意外冲突:美国,中国以及错误叙事的碰撞》(Accidental Conflict: America, China, and the Clash of False Narrativ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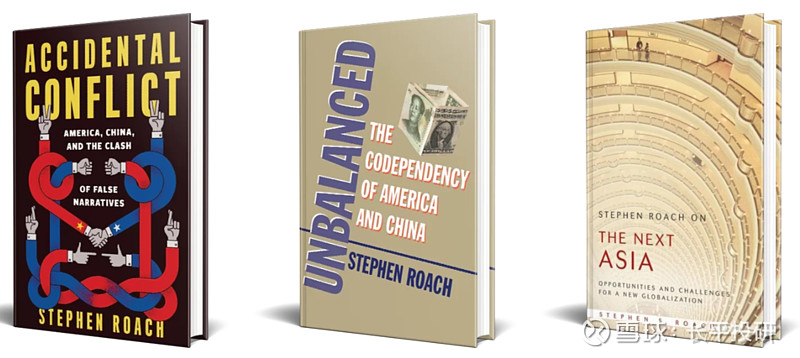
他还是忘不了中国经济。上个月,他发表文章China’s Imagination Deficit(全文在此:网页链接{China’s Imagination Deficit - Stephen Roach - CHINA US Focus})。文中作者自称是“过去25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一个顽固的中国乐观派”,但他承认自2021年开始产生系列严重怀疑——现在,当面临趋向通缩、债务高筑、大国冲突、人口危机和创新受到遏制等严峻现实时,却看不到中国有“对棘手问题的富有想象力的解决方案”、“突破性的改革”。
他委婉地说,“如果没有一种更具想象力的经济管理方法,中国可能会继续停滞不前,无法鼓起其改革者在过去取得如此成功的勇气。”
有中国学者读后说:罗奇变了。
其实,变的何止是罗奇。
朱长征
2024年春节于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