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利用长线风险资本持续支持知识产权的创新创造,将最终推动中国在与全球国家的竞合中,持续保持领先地位。
作者为凯思博投资创始人及首席投资官。
01 上一次改革给今天的启示
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始于40年前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征程。会议推出的多项改革措施,时至今日对中国经济发展仍具有深远影响。
其中,生产要素改革是意义非常重大的一项改革内容,为生产力带来了真正的解放,激发了人们生产和创造的活力。
我们知道,维系国民经济运行与市场主体生产经营活动,离不开各种社会资源,即生产要素。
无论是古典西方经济学,还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都把劳动力、土地和资本作为三大基本生产要素。
生产要素改革的目的,就在于如何促进更多的生产要素;通过高效利用生产要素,来解放和提高生产力,从而带动经济发展。
十一届三中全会推动的生产要素改革,涵盖了土地、劳动力和资本三方面。
土地改革方面,提出将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相分离,同时放开对土地使用权的限制。
在农业生产领域,农田使用权被放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全面实行,农民生产的积极性被激活。
在工业生产领域,民企和外企可以通过租赁土地实现扩大生产和快速发展。同时,政府也可以通过出让土地使用权获得财政收入,以支持地区基础设施建设。

资本改革方面,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在此基础上,设立了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个经济特区,推出一系列优惠政策来吸引外资进入中国,解决了经济发展需要资金的难题。
劳动力改革方面,允许人口流动和自主择业。 一时间,乡镇企业、个体户、企业承包经营等新型生产关系如雨后春笋般不断涌现,改变了以往“吃大锅饭”的分配模式。劳动力的生产效率提到大幅提升。
02 新质生产力,核心在知识产权
经过40年发展,中国劳动力、土地和资本三大生产要素的粗犷式开发和提效空间接近饱和,经济增长速度也出现调整,结构化改革进入深水区。
人口方面,我们面临老龄化的挑战, 土地财政也困难重重, 虽然资本在40年中有了极大的积累,但许多条条框框和不成熟的资本巿场限制了资本的充份利用, 改革如何突破呢?
党的二十大提出,中国经济要走高质量发展之路。为了实现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就需要培育除三大生产要素之外的新生产要素,同时围绕该生产要素,构建新的生产关系。
西方经济学理论,比如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为代表提出的新贸易理论,把技术作为第四种生产要素。
不过,在我看来,技术只有在转化为可以直接应用于生产、制造、管理等经济活动过程中的工具与权利,才能称之为生产要素。
这种情况下,技术就是以知识产权的形态存在,即IP(Intellectual Property)。因此,我认为知识产权可以是补充三大生产要素的第四种有价值、有潜力的新生产要素。
知识产权(IP)经过具体的开发和应用,可以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新质生产力的本质,即是通过构建新型生产关系,促进高质量生产力的发展。
“先进技术- 知识产权-生产力”的闭环,与新质生产力有异曲同工之妙。而这个闭环的核心在于知识产权(IP)。
如此来看,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关键在于加速推进先进技术转化来的IP的开发和应用。
目前,世界各主要大国的竞争尤其是在科技领域的竞争,很大程度上都是在IP层面展开的。
典型的例子就是,美国等国对中国半导体领域实施的“卡脖子”方略,底气就是这些发达国家在EDA、指令集、光刻机、晶圆工艺等形成了强大的IP储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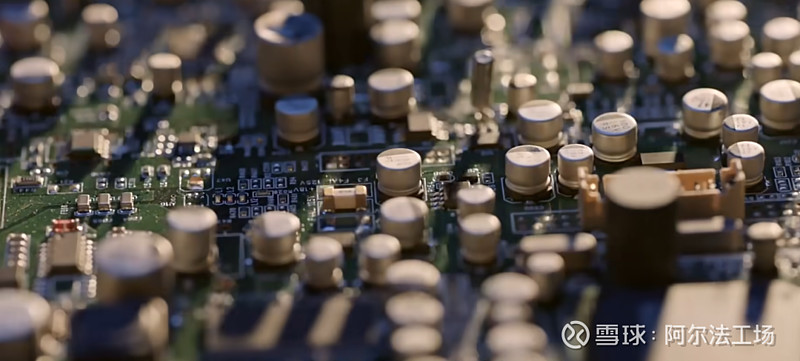
如果中国半导体行业在这些核心环节无法取得突破、形成自主IP,将很难突破这些国家设置的技术封锁,甚至恐怕长期落后下去。
展望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新一轮经济改革,必将围绕新质生产力展开和延伸。而其中一些重要的改革举措,会聚焦在如何释放知识产权(IP)的发展潜力上面。
03 新质生产力,推动力在长线风险资本
无论知识产权还是底层的技术,不像土地等生产要素是本来就存在的,而是需要人创造出来的。因此,需要一系列相互关联、配套的改革举措去培育和推动。
以改革吸引人才敢于创新的新机制,构建完整知识产权(IP)产业化体系,用市场化机制鼓励长期资本担当风险是一套完整的系统性工程,不是单单靠一两项措施,就能达到目的。
首先,IP是由人创造出来的,人才在IP开发过程中起到决定性作用。

这就需要推进人才支持政策的改革,激发高端人才的生产力和创新动力。
培育IP不仅要利用好国内人才,还有借助国外优质技术人才。
一些利于人才流动和吸纳的政策,想必会有助推效果。比如,放松国内一线城市对户籍的管制限制。鼓励国内企业在海外建立研发基地、通过绿卡政策吸引海外优质研发人才来华发展等等。
此外:我们要培养社会对创新,创业失败的容忍度。对于创业失败的人,是否都要用“失信”来惩罚呢。
其次,IP的创造和开发等环节,不仅需要花费比较长的时间,而且需要持续的资金“输血”,过程中还伴随着较大的研发失败的风险。
这就需要大量且稳定的长线风险资金,支持IP的前期创生。 这就需要改变目前金融机构普遍的风险厌恶到风险担当。
一个有效的途径,就是学习新加坡经验,借鉴淡马锡模式。
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邓小平在著名的“南方谈话”中已明确提出“借鉴新加坡经验”。
为了学习新加坡的工业化成功经验,中新两国合作在苏州打造苏州工业园、并成立专门的协调机构——中国-新加坡苏州工业园区联合协调理事会。
30年后的今天,我们应该再次学习新加坡的成功经验,设立“中国版的淡马锡”。
简单来说,就是在国家层面出资,集合民间资本和国际资本,用市场化手段设立长线风险投资机构或创业投资机构,主要聚焦于先进技术的IP转化以及IP的开发、创造及商业化应用开展长周期、高风险的投资活动。
5月23日,总书记在山东主持召开企业和专家座谈会。
本次座谈会邀请了安踏(2020.HK)、传化和博世等民企和外企的负责人,以及投资机构深创投的负责人。
联想到下个月即将召开的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此次座谈会传达的信号,颇有深意。
在本次举办的企业和专家座谈会上,有来自深创投等投资机构负责人谈到了“发展风险投资”的内容;安踏和传化等民营企业负责人则发表了以“用科技改造提升传统产业”为主题的发言。
在某种层面上,这透露出未来经济改革的一个重要信号,就是如何利用长线风险资金来释放创新活力。
比如安踏,如今已经不仅仅是一家体育用品制造商,更是一家体育科技装备的研发公司。
安踏一年研发投入高达16亿,在全球建立了5大设计研发中心,相继研发出了安踏膜、柔心纱、儿童骑行服、国家队竞技装备等一系列科技IP成果。
传化集团更是在智能物流领域打造出无人化、数字化、标准化的智能云仓,并研发出“中国物流大脑”、“鲸眼系统”和“风豹2.0”等智慧物流黑科技。
座谈会上,德国博世(中国)投资有限公司总裁徐大全,分享了企业知识产权在中国得到有效保护的故事,并就优化外资企业营商环境提出了意见建议。
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护创新。
总书记在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五次集体学习时强调:“知识产权保护工作,关系国家对外开放大局。”
令人欣喜的是,无论保护机构还是保护机制,中国正在逐步完善一整套知识产权保护“社会共治”系统,不断塑造“新质法律保护与监督能力”。
过去十年来,中国对专利法、商标法、著作权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等知识产权专门法律进行了多次修改;在北京、上海、广州设立知识产权法院,构建出全方位、立体化保护的知识产权法律体系。
近日,随着国家知识产权局等9部门联合印发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建设工程实施方案》出台,截至目前,全国已布局建设国家级知识产权保护中心71家,快速维权中心42家。
但我们也应看到,AI等新技术发展日新月异,知识产权领域的新挑战将层出不穷。构建适应本土技术发展的治理系统,同时加强全球合作、开启对话与交流,是未来全球IP共建生态体系的核心。
截至2023年底,博世在中国设有34家生产基地和26个技术中心,当年投入研发费用达110亿人民币,亦参投多个中国汽车产业链项目,充分体现了“走出去、引进来”共同发展下,互通有无、链接共融的IP国际化。
“国际IP本土化”和“中国IP国际化”——两者共建共融,是一种更高层次上的知识产权保护,也是能真正引导产业深度转型升级的高质量创新。
总结起来,以政策吸引和留住高端技术人才,并利用长线风险资本持续支持IP创新创造,将使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战略落到实处,充分呵护IP成长,最终推动中国在与全球国家的竞合中,持续保持领先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