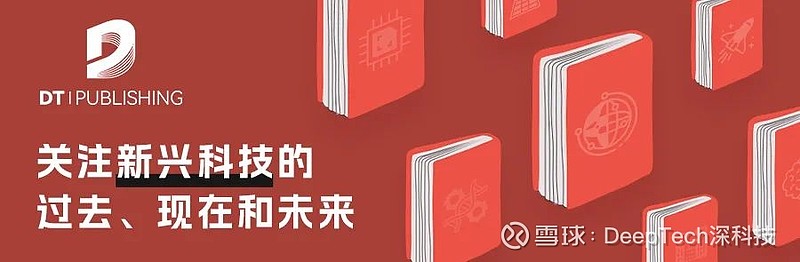
作者:泡菜
编辑:YCZ
科研往往是积年累月无穷无尽的失败,突然间命运垂青,就会大有进展,不然就似乎是永恒的黑暗。这种节奏在其他任何领域都只会令人发疯,因此耐心与超脱是必需的。
学过大学化学的同学们应该还记得马丁·卡普拉斯(Martin Karplus)二面角公式,学过有机合成的盆友肯定忘不了罗伯特·伯恩斯·伍德沃德(Robert·Burns·Woodward)巧夺天工的维生素B12合成,而从事化学生物学研究的朋友们也一定会对斯图亚特·L·施莱伯(Stuart L. Schreiber)这个名字很熟悉。这些鼎鼎大名的科学家们拓展了科学的边界,仿佛如何称颂都不为过。
然而,你能相信后来得到诺贝尔奖的卡普拉斯被人炒鱿鱼嘛;你能想象伍德沃德被学生用轿子抬着去上课嘛(然后晚年沉迷于打牌到深夜);而伍德沃德的关门弟子施赖伯又是抢功劳,又是被人笑称为“衰伯”......
这些“黑色历史”以及更多的黑历史,大多与一家名为福泰(Vertex)的制药公司有关。而这些已在各自领域闪闪发光的名人当年被召集一起,均是因为一粒价值十亿美元的分子药物。

一粒药丸引发的战争
十亿美元,是上个世纪80、90年代一款成功的畅销药物所需达到的年销售额。创造出价值十亿美元的分子药物是那个年代富集在波士顿的顶尖科学家、创业者与投资者的共同目标,这群性感大脑们纷纷将自己的智力、见识、金钱与青春,全部投注在这场豪赌当中。在生命健康领域呈井喷态势的今天,这个数字已经上升至百亿。然而,与两年前的巨大繁荣有所不同,2022年前三季度,医药股表现都很低迷。但在三十年前,正是在同样的低迷当中,乔舒亚•博格(Joshua Boger)一手将福泰塑造成制药界的黑马。至今,福泰制药依然是世界前30的顶级药企,市值超过500亿美元。
博格在35岁便成为世界首屈一指的药企——默沙东的基础化学部高级主管,意气风发的他在当时被认为是以后能够执掌默沙东每年10亿美元研究经费的有力人选。尽管如此,他在1989年选择出走老东家,创立福泰制药,并以“理性药物设计”(rational drug design)为理念研发全新药物。
彼时,全世界的药物研发还延续着传统的“组合化学”方法,通过大量合成、大量测试、广泛筛选的方法搜寻新药。这种依靠穷尽所有排列组合可能的方式,找到能够作用于特定靶点的药物,强烈依赖运气而近乎于大海捞针。
而博格则是想以一种新的基于结构的药物研发范式来打造他的十亿美元分子。随着解析蛋白质结构的技术手段不断成熟,生物学家们能够依靠分子结构来推算其功能,结合计算机的快速分析与推演,理论上则能迅速还原药物分子在蛋白质分子上的靶点的作用过程,从而理性地设计药物。这,便是默沙东逆子博格在不惑之年选择出走并创立福泰的原因。

默沙东逆子出走后怎样?
离开默沙东后,博格很快把目标聚焦在了免疫抑制剂的研发和升级上。器官移植以其鬼斧神工之力让无数原本等着被审判的生命获得了二次重生的机会,被认为是现代医学创造的奇迹。该技术在20世纪90年代初趋于成熟并迅速发展的原因之一,便是各大药企竞相研发免疫抑制剂,从而有效地解决了移植后的排异问题。博格也在该队伍中,他的目标是重新设计免疫抑制剂FK-506——一个在抗排异方面有着奇效但却表现出强烈毒性的药物。博格看到了KF-506的潜能,他想要降低其毒性,将其打造为完美分子。
现在,他手上仅有1000万美元的风投资金和十余名科学家,每周却要烧掉近10万美元,并且初期并无任何科研成果。而他的竞争对手则是肝移植之父斯塔泽、化学生物学先驱施瑞伯,还有美国科研实力最强、最受敬仰的药企、他的老东家——默沙东。面对这样的境况,乔舒亚•博格该如何破局?
“健康的人比病人多,因此我们要给他们做点药。” 抱着这样的信念,他召集了所有能创造未来的人。然而事情并非一帆风顺。
一位曾为《纽约客》《纽约时报杂志》《智族》《户外》等多种报纸、杂志撰文的美国记者巴里•沃思(Barry Werth)在福泰成立之初便住进了福泰制药成员家中,以第一现场在线吃瓜的距离,看到了最真实的药物研发过程,以及福泰内部最成功的科研与最成功的商业之间的激烈碰撞:总裁团战科学家,高级科学家欺压初级科学家,科学家和业务官互相不爽......
尽管沃思见证了这些看似狗血甚至令人瞠目结舌的黑历史,但在他眼中,这反而突显了福泰员工们对“开发新药”这个一致目标的坚定追求:科学家有的几乎住在公司中赶实验进度,有的自愿献血以提前完成实验,业务官则与在日本的对手24小时连续不断的谈判......而这些,可能正是所有被光环笼罩的独角兽公司的真实日常。
结果如何?最终福泰失败了,FK-506的研究进程不仅落后于竞争对手施瑞伯,而且从根本上,他们最初猜想的FK-506的作用靶点FKBP-12被施瑞伯证明是个完全错误的方向,十亿美元分子的梦想彻底幻灭。但即使这样,福泰也成功了:其无心插柳的另一个艾滋病毒抑制剂项目获得了成功,并经过三年的淬炼,福泰获得了投资人与市场的信任,成功上市。今天,福泰制药股价215美元,市值逾500亿美元,年营收超30亿美元。

编辑荐书
1994年,巴里•沃思出版了《十亿美元分子:追寻完美药物》一书,将福泰在与各路大佬恩恩怨怨的纠缠中,从一家只有概念的创业公司到在纳斯达克敲钟上市的故事讲述给大众。之后,续作《解药——走进制药新世界》问世,进一步记录了他们如何真正开发出两款上市药物,切实挽救患者生命的故事,其中他们与患者组织囊性纤维化基金会合作研发的罕见病药物堪称商业价值和社会价值双赢。
这本书的魅力在于,它没有过分渲染科研的道德高尚或粉饰商业逐利的本质,而是真实地将科研过程的艰涩,科研与商业之间的博弈以及企业间的残酷竞争还原出来。只有对知识的渴望、对利益的追逐这些原始的欲望才能促使一项科学研究前进一小步,而这往往还可能只是偶然的一小步,便能创造巨大的商业价值并改变很多人的生命。
作者巴里•沃思进驻福泰公司内部四年之久,在剑桥期间,他住在晶体学家梅森·山下的家中。他对山下的刻画,也十分生动:
科学是严谨有序的,这种秩序根植于亚原子领域最小、最细微的力中。只要足够细致,人们可以看到它、理解它、操纵它。“相比之下,我们的手势如此的笨拙,” 他说,“但我们的手可以指挥数十亿的分子来做同一件事,比如拾起或放下一个氢原子,这太神奇了。” 山下认为,亚原子之间的相互作用是人类行为的完美典范,他弹指一瞬的生命也应当如此。在他看来,人群的熙熙攘攘也受简单的结合力的控制,就像加缪在《鼠疫》的结尾处所写的:“在他们唯一的共同信念的基础上站在一起,也就是说,爱在一起,吃苦在一起,放逐在一起。” 精确将带来真理,甚至救赎。
只有一个限制条件:必须绝对正确,不然一切就会土崩瓦解,坍塌为熵与痛苦。
山下对光谱学寄予厚望,然后怀着信念跃向万千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