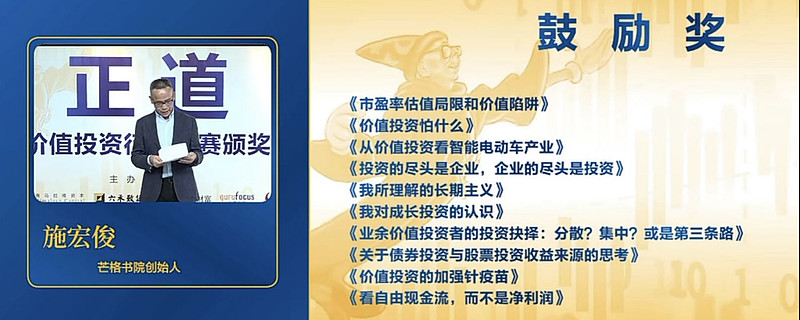
摘 要:
对于业余价值投资者来说,是采用分散策略,还是采用集中策略,这是必须要回答的灵魂之问。
以格雷厄姆、施洛斯为代表的经典价值投资派,推崇分散投资组合。这类主要聚焦财务报告研究的投资方式,需要对大量分散标的投入研究精力。但业余投资者在执行分散投资策略的时候,难以对如此多的投资标的投注充足的时间。
以巴菲特、芒格为代表的现代价值投资派,推崇集中投资策略。这种策略从估值出发寻找有安全边际的投资标的,然后从关键问题入手求证估值修复的可能性。作为业余投资者,因为没有短期业绩压力,具备践行集中投资策略的先决优势。但当长期没有找到投资机会时,个人资金闲置带来的机会成本就不能被忽视了。
本文针对业余价值投资者的特点和资源禀赋,提出了“以指数投资为主的资产配置组合+集中投资”的投资思路,并尝试结合案例说明业余投资者如何在所在行业的产业链上下游建立能力圈,应用集中策略开展价值投资。
1984年,巴菲特先生在纪念《证券分析》出版50周年座谈会上的发言中,介绍了包括自己和芒格、施洛斯等在内的数名取得了长期业绩的“超级投资者”。哥大的布鲁斯▪格林沃尔德教授进而将格雷厄姆、施洛斯划为经典价值投资派,其推崇分散投资组合;而将巴菲特等划为现代价值投资派,其推崇集中投资策略。对于业余价值投资者来说,是采用分散策略,还是采用集中策略,这是必须要回答的灵魂之问。
1.关于分散策略
众所周知,价值投资的鼻祖——格雷厄姆先生在上世纪中叶提出了“安全边际”的概念,并指出安全边际与分散化原则有着密切的逻辑关系,因为投资者即使有一定的安全边际,他所投资的个别证券还是可能出现不好的结果。因为安全边际只能保证盈利的机会大于亏损的机会,并不能保障不出现亏损。但是,当能购买的具有安全边际的证券种类越来越多时,总体利润超过总体亏损的可能性就越来越大。(《聪明的投资者》第20章 作为投资中心思想的“安全边际”)
格雷厄姆的学生沃尔特•施洛斯终生坚守这种分散策略,他在访谈中对自身的投资能力表现得非常谦逊和诚实,承认自己没有足够的能力去识别那些有长期发展的好公司。因此他专注于传统格雷厄姆式的价值投资思路,基于资产负债表进行分析评估,采用分散策略选购廉价股。在管理基金期间,施洛斯父子的投资组合中保持100支股票数量,但其中最大的的20支他在投资组合中占比约60%。
笔者根据访谈资料,将施洛斯的投资流程概括为“五步法”。首先用股价走势来筛选一个大致的股票范围,找到股票价格处于两年或三年来的低点的标的。第二,找到售价不到营运资本2/3的股票,从中剔除债务负担重和大福亏损的企业,少量买入。第三,深入研究公司年报,保自己已经透彻地阅读了公司年报,包括附录和脚注,确保公司不存在严重的财务负债,同时识别表外资产。第四,在持股行业内进行扩展研究,分析这个行业的其他公司,卖出品质差的,转而买入品质更好的。第五,持续跟踪择机卖出,在廉价股开始上涨并超出价值区间时选择卖出,另一方面,当资产或者盈利能力的恶化超出预期时选择抛售。
施洛斯老爷子就是这样干了一辈子“捡烟蒂”的活计,购买具有安全边际的股票组合。这种分散策略本质上是在具有安全边际的股票上“广撒网”,在下有保底的情况下等待股票组合中的个别股票出现爆发性的超额收益。他曾在访谈中提到自己投资西太平洋(Western Pacific)的例子,这家公司本是组合中一个具有安全边际,但没有什么前景可言的公司。但在施洛斯持有该股票期间,西太平洋并购了一家油泵计数器公司。当时汽油价格大涨,超出了市面上计数器显示的最高金额99美分,所有计数器都要更新,这家生产油泵计数器的公司顿时业绩大增,带动了作为母公司的西太平洋公司业绩增长。施洛斯在这支股票上取得了超额收益。(1989 《杰出投资者文摘》)如果通过函数来表示施洛斯投资组合的收益率分部的话,这应当是一个正偏正态函数(如下图所示)。即由于少数取得超额收益的股票,拉升了整个股票组合的投资收益。
不少业余投资者认为格雷厄姆、施洛斯式的分散投资方法简单易行,甚至仅仅依据资产负债表数据来进行估值分析,对此笔者持怀疑态度。因为在当前的市场条件下如果仅从资产负债表数据出发,难以发现企业的表外负债和表外资产,同时将不同的会计政策下的财务报表进行对比分析会对分析结果造成较为重大的不良影响。而这些方面的研究恰恰是需要投入大量精力的关键工作,业余投资者在执行分散投资策略的时候难以对如此多的投资标的投注充足的时间。
2.关于集中策略
在《穷查理宝典中》收录了芒格先生诠释了伯克希尔哈萨维践行的集中投资策略。他指出“我们的投资风格有一个名称——集中投资,这意味着我们投资的公司有10家,而不是100家或者400家。我们的投资规矩是等待好球的出现。
作为集中策略的践行者,李录先生在2006年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的讲座上曾分享过一个关于“添柏岚(Timberland)”的投资案例。(《文明、现代化、价值投资与中国》价值投资的常识与方法——2006年在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的讲座)
第一步,从资产负债表出发进行初步研究。李录先生发现这家公司的市值在净资产附近,账面资产是干净、保守且有流动性的,账面上有1亿的现金资产和1亿的房地产,这两块资产的价值约占市值的三分之二。同时企业运营情况良好,每年有约1亿的息税前利润,资本回报率(ROCE)高达50%。
第二步,找出其低估值的原因,以问题为导向一一验证。李录先生发现这是一家家族控股企业,家族拥有40%的股权和98%的投票权,同时发生了有关少数股东的诉讼案件,这造成了资本市场对公司运营的不信任。因此李录先生提出的关键问题是——是否存在管理层挪用公司资金或伪造账目的情况?作为一名公司经营的局外人,价值投资者通常难以拿到第一手的财务数据。因此李录先生转而去从侧面调查,通过了解、评判管理人是否值得信赖,为公司账面的真实性提供旁证。为此,李录先生经过多方调查,期间还通过私人关系加入了一家公司CEO任董事的公益组织,这段同在公益组织董事会的经历令李录先生真切地感受到了创始人家族的正直和优秀。解决这个关键问题之后,李录先生决定下重金购买添柏岚公司的股票,在市场观点扭转后,该标的股票的估值翻了3倍。
在上面这个投资案例中我们可以看到,李录先生在从资产负债表出发进行初步研究的过程中,做的工作与施洛斯在投资前做的研究基本一致。如果只在第一步研究的基础上开展投资,那么这将是一个具有安全边际,但胜率不足的投资标的,应当采用分散策略严格控制仓位。
以上结论也可以通过简单套用凯利公式来说明,相关数据建立在假设基础上,仅供参考。在凯利公式中,设成功概率为p=30%,成功后净收益比例为b=3,失败概率为q=1-30%,则最佳仓位应为f=(bp-q)/b=6.67%。属于分散投资策略下的仓位比例。
但在第二步深入研究之后,该笔投资的关键风险问题得到了解决,进一步确定这项投资不是所谓的“价值陷阱”,投资胜率随之大大提升。我们设设成功概率为p=70%,套用凯利公式得出最佳仓位应为f=46.67%,也就是可以应用集中投资策略了。
上面的投资案例诠释了践行集中策略的大致过程,就是从估值出发寻找有安全边际的投资标的,然后从关键问题入手求证估值修复的可能性。作为业余投资者,因为没有来自投资机构和投资人的短期业绩压力,践行集中投资策略就具备了先决优势。如果能在自身熟悉的行业或专业领域持续开展投资研究并形成能力圈,那么就可能在能力圈内形成价值投资的专业能力。但对于业余投资者来说,需要及时发现和识别有价值的投资标的,并取得有价值的研究结果,这既需要市场机遇,也需要个人能力圈的保障。那么如果在一段比较长的时期内,在自身能力圈范围内没有遇到适合的投资机会,那么由于资金闲置带来的机会成本就不能被忽视了。
3. 第三条路:资产配置组合+集中策略
正如李录先生指出的(《投资的知行合一-2019年11月在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的演讲》),经济体内的规模以上公司的平均利润通常会稍高于经济体自身的名义增长率,因此指数投资在指出可以大致反映整个经济体平均表现的情况下,是一种值得长期持有的投资工具。个人价值投资者完全可以搭建一个以指数投资为主的资产配置组合,作为常规的投资方式,在发现集中投资机会时,再适时开展集中投资。
在资产配置组合方面,一是搭建以指数投资为主的资产配置组合。以宽基指数组合、债券类基金为主搭建资产组合,重视现金资产的储备。由于两者之间存在弱相关性,使得配置组合的夏普比率(Sharpe Ratio)相比指数投资有了较大的提升,相对降低了波动率。 二是应用相对估值指标进行指数投资的调仓。可以应用股权风险溢价、市场平均市盈率估值百分位等相对指标来评价市场的估值水平。并根据相对估值的水平高低来指导指数投资部分的仓位比例。例如可以在市盈率估值百分位20%-50%的区间,可以开始以定投增仓的方式调增宽基指数在配置组合中的比例。三是做好动态再平衡。如果指数没有高估,也没有低估,那么就应践行被动投资的策略,在等待市场估值变动的同时定期进行动态再平衡,这个过程本身就是低买高卖的过程。
在集中策略方面,业余价值投资者可以结合主业工作,重点关注所供职企业的上下游范围。常劲老师曾在北大“价值投资”课上说,测评自己的行业能力圈,要看是否对某一行业具有预测力、判断力和洞察力。作为业余投资者,最容易建立认知差的地方,往往是自身正在从事的行业。当投资机遇恰巧出现在能力圈范围内,业余投资者可以调用资产配置组合中的现金资产、债券资产开展集中投资。
我们在这里设想一个案例,在国内通信运营企业供职的小D是一名业余价值投资者。2X18年,他发现行业内一家设备供应商(以下简称“标的公司”)因为企业内控问题和国际贸易摩擦的原因,收到了巨额罚单。小D供职的企业是标的公司在国内最大的客户之一。标的公司的股票在停牌多日期间,出现了自媒体集体看空的舆论信息,甚至在网上炒作标的公司将成为“继XXX之后,又下一个倒下的通信设备生产商”。复盘后,该股票连续7个交易日跌停。考虑到标的公司受行业态势影响,主要业绩指标呈现周期性变化,因此小D通过市销率对其进行相对了估值。之后,小D开展了市场信息的搜集和整理工作,他将“市场先生”的最担心的关键问题归纳为“破产风险”,“市场先生”认为在巨额罚单和贸易摩擦持续升级之下,标的公司未来的基本面已“凤凰变乌鸦”。
小D作为业内人士在对上述关键问题进行了深入调查。小D初步测算后发现,该企业在支付巨额罚单后,不考虑其他因素,资产负债率将突破70%,但该企业长期负债经营,这样的资产负债率水平并大比例偏离历史水平。此外,在舆论发酵的那段时间,小D发现在办公楼里经常能见到自己的一位前同事,这位前同事在辞职后去了另一家设备运营商,是标的公司的主要竞争对手之一。这位前同事透露,最近运营商普遍存在一定程度的项目押款情况,并抱怨研究标的公司似乎获得了“优先付款”权,同时连中大项目。在针对标的研究期间,小D还通过公开渠道得到了国内多家银行向标的企业提供贷款的情况,该信息也在小D与标的企业客户代表的交流中得到确认。自此“破产风险”问题不攻自破,小D决定对标的公司进行集中投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