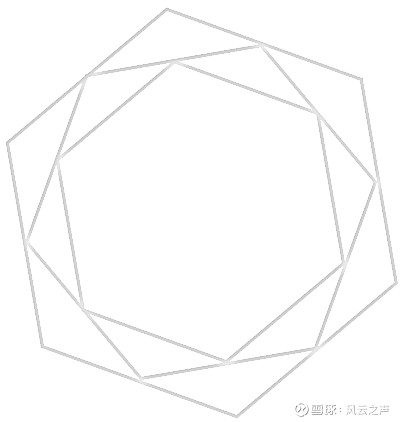
关注风云之声
提升思维层次
导读
在很大程度上,鲁莽地“减负”是教育者在逃避责任,逃避那些真正有益于学生却会给老师和学校增加负担的责任;而要求初等教育简单地“减负”则是家长、社会管理者、乃至整个社会在逃避我们塑造良好氛围,花更多地时间、精力,更耐心,更重视、鼓励中小学生学习过程的责任。然而,我想这大概是我们最承受不起逃避的责任。
注:风云之声内容可以通过语音播放啦!读者们可下载讯飞有声APP,听公众号,查找“风云之声”,即可在线收听~
对于中国的基础教育来说,“减负”已经是老生常谈了。关于“减负”我们究竟在讨论什么?我们现在的做法好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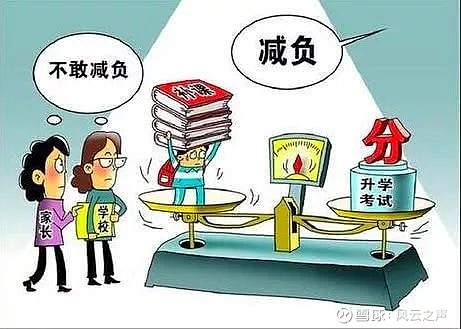
基础教育应不应该“减负”,这是个伪命题。
什么是负担?当一个人因为做一件事感觉有压力,感觉不愉快,这是感觉到负担。我很少听人抱怨:“这游戏太好玩了,我觉得好累!”,“好电影太多了,我需要烂片!”如果有,八成也是在开玩笑或是偶尔寻找调剂。一个人发自内心地喜欢做什么事情的时候,他/她是不太容易觉得做这件事是有负担的。人一般不需要任何外在的激励就会为自己喜欢的事情心甘情愿、快快乐乐地投入时间和精力(e.g. Black & Deci, 2000)。所以,所谓“减负”的问题不在“减”这个字,而是学习怎么成了负担?基础教育的设计者、决策者,从来就不应该重点关心学生课业的多少,而是应该关心学生为什么不爱学习。中小学生不是因为课业太多了,觉得有负担,就像他们不是因为游戏太多了,所以不想玩一样。
实际上,我个人并不反对基础教育方面的改革,尤其是“以学生为中心,全面发展的基础教育改革”。我支持罗杰斯(Carl Ransom Rogers)人本主义教育的原因,不仅仅因为学生人格的健全,潜力的充分开发有心理学意义,更因为这对我们整个社会有着深远的影响。文艺复兴提出的“全人教育”对社会各方面的进步都起到了根源性的作用。然而,我非常反对将“迈向全面发展的教育改革”用“减负”来符号化。现在教育改革的方向应该是:1)在掌握知识的同时,培养学习的热情;2)在了解结论的同时,学会研究的方法;3)在具备实证检验能力的同时,具备逻辑论证的能力。而这一切和所谓“减负”并没有什么必然联系。

Carl Ransom Rogers
“爱上学习”对现代人来说越来越重要。
现代社会发展很快 。如果不及时更新知识,很容易被淘汰。有亲友的孩子要读博士,就问我“现在的人得学到什么时候啊?学完习,半生都过去了。”不是半生,而是一生!现代人的一生就是不断学习的一生。如果非常痛恨学习,那的确是痛苦的一生啊!美国《独立宣言》里面提到三项天赋人权(unalienable rights), “生命”、“自由”、“追求幸福”。仅仅是为了让学生幸福地度过一生,仅仅是为了他们的快乐,也应该努力让他们热爱学习,不是吗?
其实,终身学习有何新奇呢?我们的大脑一生都是活跃的,不断改变的。什么时候一个人的大脑停止改变了,他/她也就生物性地死亡了。所以我们人类原本就是一生都在学习啊!认识新的人,认识新的事物,只要活着,就不会休止。但是让一个人爱上数学是很难的,减少数学考试,禁止数学竞赛,这就要容易多了。简单地“减”,这是教育工作者在逃避责任了。
基础教育的“减负”有大伤害。
我们先从学生的角度来看看“减负”的伤害。虽然人类的大脑一生都是活跃的, 能够学习的,但其活跃的程度在人生的不同阶段是有很大差异的,有关键期。我们从出生到成年,身体会增大20倍,大脑却只增大4倍。如果一个学生年轻的时候没有充分地利用大脑的潜能,学习关键性的知识,那么未来的学习只会更加艰难,生活会更加不易(Rakic, 2002)。
从家长的角度来看,现代教育与古代教育在其社会性上,一个很大的区别在于古代的教育更加私人化,知识传播的责任在家长。如果家长愿意多投入资源,那么骑马射箭也好,琴棋书画也罢,孩子自然都是可以学。但是现代社会的教育是把教育责任公共化,从而提高了社会公平性,也解放了家长的生产力。如果一个学生没有充分利用在校时间来学习,而其知识的获取更多地依靠“私学”,那么社会的公平性就大打折扣了。设想一个家庭条件很差,父母很少在身边的孩子,减少了课业,多了自由支配的时间,而又没有爱上学习,那么他/她会在自由支配的时间里干些什么?更有可能读读《时间简史》还是打打“王者荣耀”?
时间是公平的,有限的,固定的。强大的公共教育是发展中国家保障社会公平的有效措施。发达国家的孩子,放学以后可以自由地选择体育锻炼、艺术学习、兴趣培养等等这些活动,也是因为他们有足够的资源做这些事情。英格兰的国家队踢的怎么样暂不讨论,但是英国中小学生放学以后踢足球是去俱乐部,由薪水很高的专业教练指导练习的,可不是上蹿下跳、满大街撒欢自己踢着玩的。在资源不够充沛,更不够平均的发展中国家里,所谓“减负”对那些较为弱势的家长而言是把“负担”转移到了他们身上。因为,即使社会真的很重视“素质教育”,难道谁弹琴弹的更好,舞蹈跳的更棒,就没有相互的比较了吗?如果公共教育推卸了责任的话,大概率情况下,谁的资源投入更多,谁的产出效果就更好,不是吗?让没有足够专业知识的家长们来主导孩子的素质教育,“量子波动速读”、“行为矫正学校”这些乱象的出现还不正常吗?
从国家与社会的发展来看,“减负”有大伤害。我们刚才讨论的这些,并不非常适用于作为异常值的天才们。较少学业考核的内容和难度,让学生们自由地利用时间发展天赋,对于天才而言,的确是个好事,所以像美国、日本这样基础教育比较轻松的国家,也仍然培养出很多天才的科学家、数学家,因为这些天才可以因地制宜地充分发展自己的天赋。但问题是,天才不会因为课业减少成绩变差,其他人就不是这样了。
从一个国家的角度来看,一两个天才的诞生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其落后的面貌。越南培养出了吴宝珠这样的菲尔兹奖得主,这是不是说明越南的数学水平比中国高呢?恐怕不是。培养出大师当然是好事,但一个国家的整体发展,不是一两个大师足以决定的。人类的生物属性决定了,天才的时间和精力也是有限的。不是天才的人当中也有大量的人热爱科学,从事科研相关的工作,不是更好吗?实际上,往往有足够多的普通研究者,天才才能被解放出来做那些最有突破性的、最重要的研究。普通的人,如果不热爱科学,不从事科学工作,就能成为优秀的歌手、演员吗?恐怕那些工作更需要天赋。
在世界经合组织(OECD)所主导的,针对全球79个国家15岁学生“阅读”、“数学”、“科学”能力的评估项目,PISA(Programme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2015-2016年度的报告中可以看出,基础教育以往备受诟病的东亚国家和地区几乎全部名列前茅,新加坡第一,香港第二,日本第三,澳门第四,台湾第七,韩国第九,中国大陆第十。但是,这并不是说,我们儒家文化圈的基础教育就是完美的。接下来,我从组织行为一些流行理论的角度来分析一下,我认为哪些教育政策或措施是不可取的,哪些又是应该做的。
1. “禁止分班”不但不是“有教无类”,更违背了“因材施教”。
西欧发达国家的基础教育仅略微落后于东亚,但在西欧国家中,荷兰、德国、瑞士三国是成绩最好的。我教的学生大部分是欧洲人,PISA的报告与我个人的观察一致度很高。在我看过PISA数据以前就有这种感觉,实行分班制、差别教育的中欧三国学生个人素质和基础知识都要好于其它欧洲国家。这三国中学的分班是自由选择的,但是如果你跟不上进度,老师是会劝你改换班级的。例如,你可以自行选择经济学或物理学,但物理学班级的数学要求比较高,如果你跟不上,可能会被老师建议改成经济学。根据我的学生反映,如果出现跟不上的情况,基本上都是因为数学跟不上,所以学生们在各个学科中,最关注的还是自己的数学成绩。这套以数学为核心的系统是自然形成的,根据这三国学生的反映,很少听到学生或家长表示不满。
分班学习实际上遵循了人类发展的特质理论(trait theory),认可了人类在基因和社会化作用的影响下会形成特质上的差异(e.g.McCrae, 2004)。事实上,有研究表明,即使仅仅是学生的注意力也有基因上的差异(e.g. Rueda,Pozuelos, & Cómbita, 2015)。基于人的这些特质上的差异进行差异化的,匹配为原则的教育,这就是所谓“因材施教”。所谓“不患寡而患不均”,这种思维方式是建立在生产力不进步,教育资源不增长的基础之上的。分班在中国遭到抵制的原因,并不是因为差异化的教育有什么问题,而是一旦被分到“数学/科学”比较弱的班级,学校和社会就开始减少对这些学生的资源投入。所以问题在于减少的资源,而不是教育的差异化。教育工作者应该注意到,学生的天赋有差异,那么投入的资源种类也可以有差异,但总量不是必须减少。
社会比较理论(social comparison theory)认为,我们人类天然具有和他人比较的愿望,即使不比较财富也会比较智力、能力、社会影响等等(Festinger, 1954)。这种更喜欢向上比较的天性,使得我们为了缩小差距而付出努力(Suls & Miller, 1977)。当应该努力进步在学生中达成共同认识,形成一种氛围,那么大家都会互相学习努力进步了(e.g. Anderson & West, 1998; Denison, 1990)。这种氛围只要引导恰当,对于学生的发展是非常有帮助的。
学校的教育应该尊重学生差异化的客观规律进行差异化的匹配,如果简单的取消分班,实际上仅仅是用平均主义的假象掩盖了投入总量的不足,这也是教育工作者,乃至整个社会的怠惰和逃避责任了。
2. 减少考试的频次、难度、统一性并不是进步。
又是以德国、荷兰、瑞士的考试为例,10年级的考试(相当于高一)持续整整一个星期,然后学校按照学生各个科目的成绩进行录取,平时也会经常根据学生的学习状况进行阶段性的测验。
测验本身的目的是检验学生学习的状况,帮助学生改进学习方法,这并不一定会增加学生的压力。导致本末倒置的是老师、家长对测验和考试的理解。在组织行为学的期望理论(expectancy theory)里面,激励 = 期望 (认为达成该目标的可能性) * 工具性(达成目标以后获得奖励的可能性)* 效价(对奖励的渴望)(Porter & Lawler, 1968;Vroom, 1964)。也就是说一个人有没有动力做一件事情,取决于努力了有没有结果,有了结果有没有奖励,以及这个奖励多么有价值。这虽然是工作场景的理论,但是我想也适合一个人的学习。应该着重奖励那些考试成绩取得巨大进步的人,而不仅仅是考试成绩很好的人。一直单纯的看重并奖励学习成绩好的人,而不是重视并奖励进步,这是学生们失去学习动力的重要原因之一。
因此,并不应该减少考试(只要考试还适量),更不应该降低考试的难度(考试要有一定区分度),而是应该全社会由上而下地真正重视学生的进步。很多优秀的人才都曾在人生的某个阶段处于很平庸的状态,而后来快速进步的。一个能够大幅进步的人,是一个非常有潜力的人。在终身学习的社会里,一个人某一个时间点的知识水平显得没有过去那么重要了,相比之下,持续进步的能力变得更加重要,因此面向未来的教育应该高度重视并奖励学习过程中所付出的努力和学生进步的能力。
关于考试内容和难度的统一性,这也是完全必要的。我硕士在美国学习公共事业管理,那个时候很关注公共教育。我发现美国大学老师们最常抱怨的是国家没有统一的教学标准,导致不同地方的学生水平参差不齐。很多学生在当地是名列前茅的,到了大学却发现自己几乎跟不上进度,连很多最基本的知识都不具备,他们坦言中小学阶段完全学有余力,如果早知道有这些基础知识可以学,绝不会白白荒废时间去搞很多没有意义的事情。
美国有这样的问题是因为美国的宪法作为上位法没有规定政府有教育公民的责任和义务,而三横三纵的分权体制导致联邦政府没有权限干涉地方事务,如果联邦政府想要统一教学内容或水平就会侵犯到州政府的利益。但是,美国人早就意识到缺少统一教学设计的弊端,多次尝试推动覆盖全国的法案。“No child left behind”(《没有孩子掉队》)法案就是小布什任内推行的试图解决这一问题的。然而,即使是这一法案也因为事先就遭到各州利益集团的强烈抗议,而被迫成为一种表面化的工具——该法案最终通过的时候仅要求各州必须有教学计划和考核标准,但不对具体内容做任何规定。
美国的基础教育有这个问题是制度设计缺陷导致的,而美国人一直在努力想办法解决。那么我们国家近15年来盛行的基础教育去中心化,去标准化的具体原因是什么,我就不得而知了。现在某些地方的“减负”工作做得如何,我不知道,但我印象深刻的是,读本科的时候,好几次被某些地方来的同学问我老家哈尔滨是不是吉林的,是不是中国的,以及黑龙江是不是在哈尔滨。
3. 科学基础和人文基础都是必备知识,应该不断增加而不是减少。
我们都知道西方主流国家的基础教育里面有公民课,公民课的目标是培养“功能健全的”(functional)公民。至于他们具体教了什么我们暂且不谈,但是这里隐含的假设是:如果没有接受教育,公民是不会自动具备健全功能的。
作为一个文学艺术的爱好者,我却想强调基础教育中尤其不应该人为削弱数学与科学的比重。重视理工科,轻视人文素质,这样的教育的确是有弊端的。但却反映了社会现实。正是因为社会生活的需要,才催生了家长、老师、乃至政府在这些方面的大力投入。就像市场天然地具备资源优化配置功能一样,教育投入也被社会需求所调节着。人为的干预是否有效,是否有必要,我认为是很值得商榷的。
和西方流行观念不同,我作为一个文科生和文化与艺术的爱好者,认为对基础教育而言,科学知识的水平越来越高是更加必要的。因为,我们的国家正在经历工业化水平升级的深刻变革。对于一个生活在技术进步相对静止的环境中的人来说,学习科学知识没有那么迫切。然而,对于一个生活在技术快速进步,工业化水平变革性提高的环境中的人来说,缺少基本的数学知识、科学常识,会使得公民自我学习、进步的能力大打折扣。这可能就是中国当代社会试图扑灭各种科技方面谣言的努力常常显得捉襟见肘的原因之一。当民众整体具备较高的科学基础知识,能够在专家解释以后,自行、准确地判断真伪的时候,就像对病毒形成了群体免疫一样,谣言也比较容易终止了。我没法想象一个学生不知道wifi、互联网、核电站是什么,而能够在当代中国健全地生活,就像我没法想象,一个学生不知道宪法和民法的区别,不知道国旗是什么样子,没听说过李白、杜甫而能健全地生活一样。而这种科学教育的增加,随着教学经验,方法,工具的进步,并不是不可能的。增加投入难,放弃进步易,但是弃难从易的代价我们真的承受得了吗?
不过,我并不认为学习科学知识是最重要的,我认为我们基础教育的缺陷在于我们只重视解决问题的具体知识和技术,而不重视这些知识和技术是如何产生的。这一点可以说是当前儒家文化圈基础教育的通病。日本学生在PISA中表现非常好。但是,对日本学生缺少革命性的创新能力、没有批判思维的指责不绝于耳。针对这个问题,日本文部省正在考虑对大学的入学考试进行改革。目前的改革计划是减少选择题,增加开放式问题。这一改革还没有受到各高校的广泛认可因此尚未实行,但最终的折中方案很可能是在全国统一考试中保留选择题,而在各个大学自己举行的第二轮筛选中完全或主要采用开放式问答。中国的考试也一直在这方面备受批评,但这么多年来,真正突出“思维方法”、“创新性”、“批判性”的改革并不多见。
4. 好的基础教育是以逻辑为准绳的批判式的,而不是简单、粗暴、指摘的批评式的。
很多人批评中国的基础教育没有培养学生的批判式思维。这种批评没错。但我个人觉得,现在大多数中国人对“批判式思维”、“独立思考”的理解恐怕有点儿不准确。他们所理解的更多地是简单的批评、反对、追求不一样。在我教过的有限的欧洲人、美国人、拉美人、日本人、韩国人、中国人以及其它地区的人中,我发现中国学生明显有一种为了反对而反对的倾向。很多学生很优秀,头脑敏锐,可是他们经常会:1)没有疑问而提问——表面是在提问,实际上在自说自话;2)一会儿遵循一套逻辑,一会儿又违背这套逻辑——表面是独立思考,其实只是在标榜自己的与众不同;3)讨论问题情绪化,不是逻辑严谨地、完整但简洁地表述自己的主张。
这些问题,我认为是我们的教育不重视逻辑导致的。科学理论在逻辑上要能够自洽。一种假说提出以后,在未能找到实证证据之前,它的可靠性几乎完全来源于逻辑上的自洽。一段论证,其必要前题是什么?所涉概念的定义具体是什么?概念与概念间的关系是什么?论证步骤之间的逻辑关系是什么?这些都清楚了,才是一段合格的论证,有说服力的论证。我们的学生在这方面做的不够好,说明他们对科学的认识很肤浅。因此,不是要减少科学方面的教育,而是要给学生们交代科学的本质。
5. 好的基础教育是真诚的教育,不是伪善。
几乎从刚一入学(7岁左右),人类就开始具备能够识别伪善(说一套,做一套)的能力。伪善的伤害是很大的。好的社会环境是使得人们发自内心地愿意做道德的事情,但如果说的是要提高素质教育,却又把毕业以后毫无竞争力的学生扔向严峻的社会,任其一生无所作为,这样的伪善是不会实现其所声称的效果的。真正好的基础教育,是毫不避讳地让学生理解科学知识对他们未来生活的必要性,传授给他们必要的基础知识,为了他们终身的学习做好准备。只有在这个基础之上,他们才会真正地从“无知”、“无能”的恐惧中解放出来,在生存没有困难的基础之上去追求更美好的生活,思考更深的道理。
6. 把学生培养成学习导向(learning orientation),而不是成绩导向(performance orientation) 。
学习导向的人重视学习的过程,在自身进步和获取知识的过程中获取快乐和成就感;而成绩导向的人更重视最后的结果,从结果中获得快乐(Martocchio & Hertenstein, 2003)。学习与成就是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体,当你还在学习的时候,你就没法最大化你的成就,当你享受成就的时候,你也就停止学习了(e.g. Dobrow, Smith, & Posner, 2011)。因此,在一个终身学习的世界里,如果学习本身就能使你快乐,你自然会度过比较愉快的一生。如果是目标导向,就会比较辛苦。我们基础教育的改革方向,应该是把学生培养成学习导向,而不是成绩导向的人。
如何才能培养学生的学习导向呢?这就又回到了我们之前所说的,要从制度上、做法上,重视、奖励学生的进步,而不单纯是最终的结果。要让学生体验到进步的快乐,让学生自己体验、经历获取新知的过程,而不是直接告诉其结果(Martin, 2018)。从培养学生自我效能感(self-efficacy,完成某项具体任务的信心)的角度来看,由浅入深地让他们体验进步也是很好的办法(Margolis & McCabe, 2006)。
我们还应该培养学生的逆商(adversity quotient,克服困境的能力),使他们关注战胜困难的快乐,而不是困难本身(Stoltz, 1997)。我教书的学校虽然是个很小的学校,但却是日本偏差值(衡量成绩好坏的一个指标)最高的学校之一,基本上只有东京大学的水平可以和我们相提并论,考进来的学生都是很优秀的。可是,近年来中国留学生因为遇到困难而出现较为严重的心理问题,较长时间失踪,最后选择退学的事情出现了好几起。而我因为是中国人,虽然完全不认识当事的学生,也还是常常被各方叫去帮忙想办法。以我愚见,大学生的人格特质基本已经形成,如果他们在初等教育阶段养成了遇到苦难就逃避的习惯,那么想要在大学阶段再培养其克服困难的勇气就已经不那么容易了。
7. 任何学校教育都不可能完全替代家庭和社会整体氛围的影响。
近些年来,越来越多的青少年感觉精神空虚,越来越多的青少年对有害事物产生成瘾性,越来越多的中小学生不能应对挫折和打击,出现了很多令人唏嘘的惨剧。然而,这些问题的产生,很多情况下都不是学校教育的问题,而是家庭教育和社会关怀的缺位导致的。要求基础教育通过减少教学内容,降低考试难度,缩短在校时长等方法来剪除像同辈压力(Peer pressure,为了屈从同辈而产生的压力)这类的问题是不现实的(Brown,Clasen, & Eicher, 1986)。
在很大程度上,鲁莽地“减负”是教育者在逃避责任,逃避那些真正有益于学生却会给老师和学校增加负担的责任;而要求初等教育简单地“减负”则是家长、社会管理者、乃至整个社会在逃避我们塑造良好氛围,花更多地时间、精力,更耐心,更重视、鼓励中小学生学习过程的责任。然而,我想这大概是我们最承受不起逃避的责任。
后记
我不是一个教育学家,不懂杜威(John Dewey),也缺少教育心理学的知识,不是很懂桑代克(Edward Lee Thorndike)。我做组织行为学研究,在大学教工商管理的课程,只稍微有一点点儿社会心理学知识,懂一点点班杜拉(Albert Bandura)的理论,而且我没在中小学教过书,按理说没资格讨论“减负”这个话题。但我想从一个终身学习的视角,不太严谨地、软性地来探讨一下这个问题。毕竟我日常所教的大学生,很多也是刚刚完成基础教育不久。他们上大学以前所受教育的好坏,确实在很大程度上深远地影响着他们自己的一生,以及我们整个社会的未来。
扩展阅读:
南京狠查教育减负,群众很愤怒,我有一个建议 | 陈经
减负之问:我们的教育究竟要培养什么样的人?| 袁岚峰
Reference:
Anderson, N. R., & West, M. A.(1998). Measuring climate for work group innovation: development and validation of the team climate inventory. Journal of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dustrial, Occupational and Organizational Psychology and Behavior, 19(3), 235-258.
Aoki, K. The Roles of Material Artifactsin Managing the Learning-Performance Paradox: The Kaizen Case.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in press).
Black, A. E., & Deci, E. L. (2000).The effects of instructors' autonomy support and students' autonomous motivation on learning organic chemistry: A self‐determination the oryperspective. Science education, 84(6),740-756.
Brown, B. B., Clasen, D. R., &Eicher, S. A. (1986). Perceptions of peer pressure, peer conformity dispositions, and self-reported behavior among adolescents.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22(4), 521.
Denison, D. R. (1990). Corporate culture and organizational effectiveness. John Wiley & Sons.
Dobrow, S., Smith, W. K., & Posner,M. A. (2011). Managing the grading paradox: Leveraging the power of choice in the classroom. Academy of Management Learning & Education, 10(2): 261-276.
Festinger L (1954). "A theory of social comparison processes". Human Relations. 7 (2):117–140. doi:10.1177/001872675400700202.
Hok, H., Martin, A., Trail, Z., &Shaw, A. (2019). When Children Treat Condemnation as a Signal: The Costs and Benefits of Condemnation. Child Development (in press).
Margolis, H., & McCabe, P. P. (2006).Improving self-efficacy and motivation: What to do, what to say. Intervention in School and Clinic, 41(4), 218-227.
Martocchio, J. J., & Hertenstein, E.J. (2003). Learning orientation and goal orientation context: Relationships with cognitive and affective learning outcomes. Human Resource Development Quarterly, 14(4), 413-434.
Martin, K. L. (2018). Learner Centered Innovation: Spark Curiosity, Ignite Passion and Unleash Genius.IM Press.
McCrae, R. R. (2004). Human nature and culture: A trait perspective. Journal of Research in Personality, 38(1),3-14.
OECD (2017), PISA 2015 Results(Volume V): Collaborative Problem Solving, PISA, OECD Publishing,Paris, 网页链接
Porter, L. W., & Lawler, E. E. 1968. Managerial Attitudes and Performance. Homewood, IL: Richard D. Irwin, Inc.
Rakic, P. (2002). Progress: Neurogenesis in adult primate neocortex: an evaluation of the evidence. Nature Reviews Neuroscience, 3(1), 65.
Rueda, M. R., Pozuelos, J. P., &Cómbita, L. M. (2015). Cognitive Neuro science of Attention From brain mechanisms to individual differences in efficiency. AIMS Neuroscience, 2 (4):183–202.
Stoltz, P. G. (1997). Adversity quotient: Turning obstacles into opportunities. John Wiley & Sons.
Suls, J., & Miller, R. (1977). "Social Comparison Processes: The oretical and Empirical Perspectives". Hemisphere Publishing Corp., Washington D.C. ISBN 0-470-99174-7
Vroom, V. H. (1964). Work and Motivation. New York: McGraw Hill.
背景简介:本文作者为日本国立一桥大学助理教授李燃,北京大学组织行为学博士,罗格斯(新泽西州立)大学公共事业管理硕士。
责任编辑:孙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