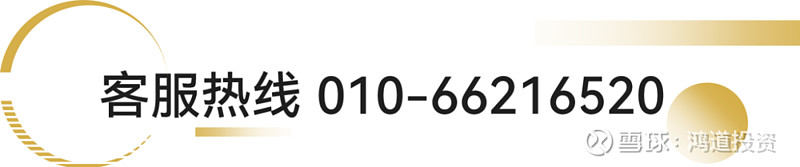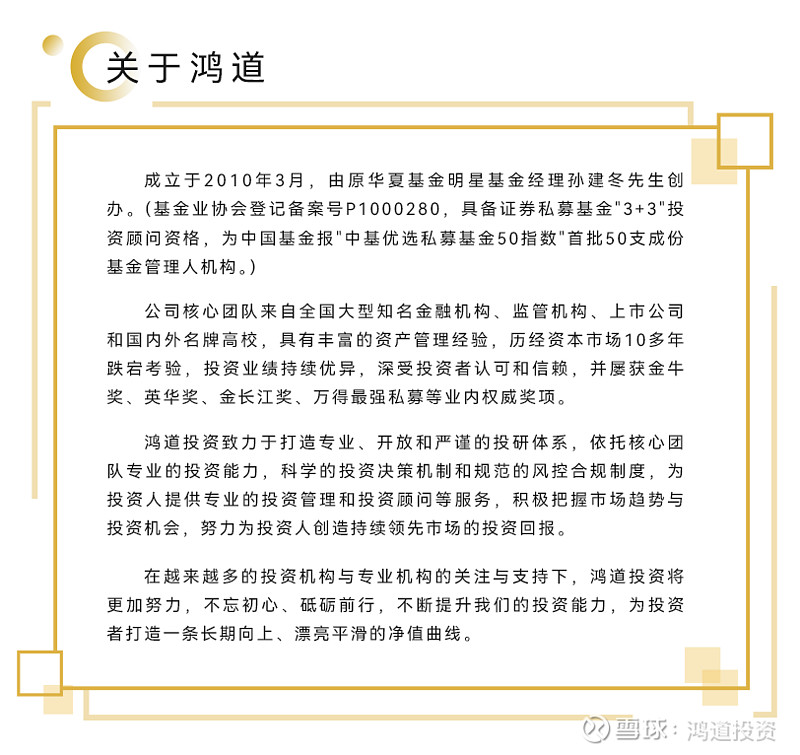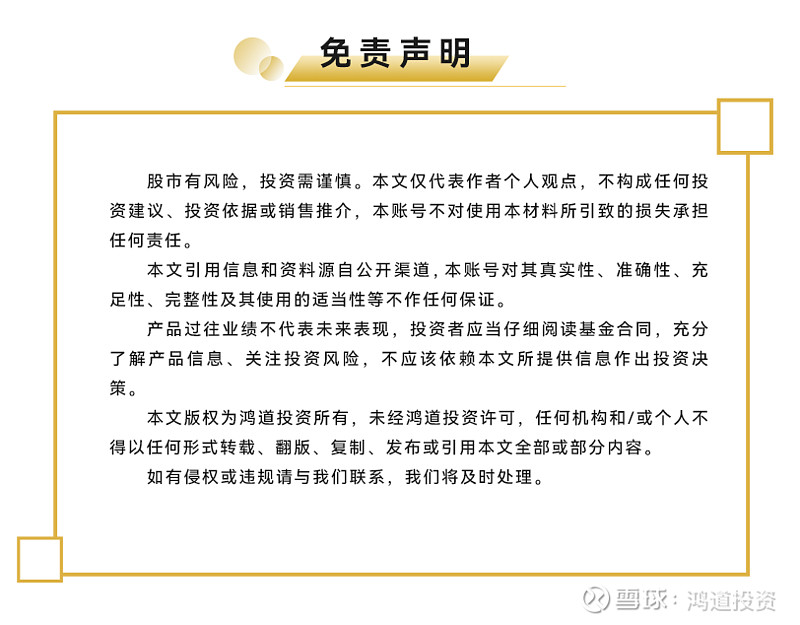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A股上证综指的表现相对于恒生指数,A股自主可控的中高端制造行业相对于消费行业均有望展现出持续的α。
这里讨论的是红利股之外的A股与港股走势的中长期差异。之所以把A股、港股有经营垄断属性的高股息股票排除在比较之外,是因为这类股票通过稳定且持续的高分红建立了绝对价值的锚。A股、港股高股息股票板块的价格走势差异,更多取决于国内背景的资金,尤其是南下资金在港股市场中的占比是否超过一个比较高的门槛。
一、A股、港股历史溢价率回归的“规律”不能机械地套用
尽管今年美联储可能会进行一两次降息,但从中长期来看,无论两党谁入主白宫,高财政支出、高财政赤字以及相对较高的利率和相对较强的美元利率会成为“新常态”(参见《美国国内政治极化与财政支出竞争性扩张的经济后果》),美债利率曲线长端下降的幅度会相对有限。相比之下,中国国内的名义利率会有历史性下降的过程(尽管过去一段时间从保护银行利差的角度,存款利率和LPR下降较慢,但名义贷款利率的下降还不明显)。中美利差的大方向跟过去十多年中国利率在上、美元利率在下的时代正好相反。过去根据“150%溢价率是港股低点、130%或者多少是港股高点”等规律来机械套用的做法,就颇有些“夏虫语冰”了。
二、香港新股发行市场长期以来单一的投资偏好导致了二级市场行业分布的高偏度及对环境变化的脆弱性
长期以来,实体经济的空心化以及香港作为中国与世界之间的桥梁,导致香港本地产业中只有地产金融行业才具有赚钱效应。香港本地投资者对地产金融行业有更深的了解和偏好。另一方面,对于全球机构投资者在投资香港这样一个离岸金融市场时,过去相当一段时间,增长动能强劲、具有稀缺性和低相关性的中国可选消费行业和互联网企业是他们青睐的对象。因此,长期时间效应累积的结果就是中国大陆在香港上市的行业,非常集中地聚焦在地产金融和互联网可选消费两大方向。对于中国在百年变局之下要大力发展的自主可控和国产替代的中高端制造业,除了创新药行业之外,其他领域则几乎没有布局。其结果就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如果十年后回顾,港股市场的行业基因与A股市场多样化的行业基因——也许,A股市场现在就类似于寒武纪时期,形成了极其不同、极其重要的历史分野。
三、美国大选和大选之后的地缘政治风险
在七八月份美国两党全国代表大会选出各自的总统、副总统候选人之后,美国大选将进入到白热化的决赛阶段。尽管民主党政府不大可能在大选前的最后阶段在中美经济关系上挑起大的事端,但是,地缘政治领域,尤其是南海,可能发生的代理人冲突还需密切关注。
通过研究1997年香港金融战的过程,明白了一个关键点,香港在国际经贸体系中的制度安排和货币制度并非内生而是外生的。
美国大选之后的2025年和2026年是美国联邦政府负债利息支付压力明显增加的两年。考虑到借新还旧策略带来的高利率债比例的上升,这两年利息支出的增量可能达到3000亿美元甚至更高。假定美国通胀和长端利率曲线还在相对高位,如果有地缘政治事件或地缘金融市场风险导致非美金融资产风险溢价的提升和资金回流美国,这对于缓解高企的美债利率无疑是有利的。
四、自主可控、国产替代的新质生产力方向相对于消费行业的长期α
相对于大力发展的自主可控、国产替代的新质生产力方向,中国的消费行业尤其是可选消费行业会经历一个较长期的筑底过程。
回顾中国过去几十年的增长模式,与其它主要国家相比,中国劳动力收入在GDP中的占比是比较低的。随着经济结构的转型,相比过去劳动密集型的行业,新质生产力行业“重资本”的特点,劳动力收入在整体收入分配中的比重会进一步降低。
如果消费品失去了价格上涨的逻辑和动力,那么除了粮食、水、电、气、通信网络以外,几乎所有其他消费品都可以被视为可选消费品。随着时间的推移,会发现“刚需”其实没那么“刚”,包括消费占比中年轻人消费比例较高的游戏。
疫情放开后一段时间,大家终于与“房价一直涨”的惯性认知做了切割,认清了“房住不炒”的现实:房子失去了期待上涨获利的金融属性,回归到只跟实际消费意愿和消费能力紧密相关的耐用消费品。最近,地产新政之后,上海二手房交易显著放量,单日成交量达到了1100套左右的水平,不过其中76%的交易是总价500万元以下的刚需型二手房。在一段时间内和一定价格区间内,对于投资需求,需求量是可变的。如果持续放量甚至因之产生了价格上涨预期,投资需求是可能变大的;相比之下,刚需总量则相对确定,一旦短期内集中释放后,后续的需求就会相应减少。6月初,上海二手房新增挂牌量创出了新高,贝壳平台上海二手房新增挂牌量以单日1400套的速度增长,这个数字甚至超过了同期的二手房成交量。
对于中国数量广大的普通居民而言,如果消费品价格没有上涨的预期,以地产为例,实际的交易量和行业景气度归根到底由居民的收入水平和居民对长期收入的预期来决定。而对于香港本地的住宅市场,更多地要看人口结构,要看中高端白领流出的速度与大陆人才引进的速度之间的对比。
对于中国的高净值人群而言,他们对房产、茅台酒和股票等风险高一些的金融资产的需求,其观察的同步指标更多要看M1的增速及其变化趋势。从两个重要的方面来看,上海豪宅市场和飞天茅台酒在本质上是同类:首先,二者都是中国过去十多年来M2高速增长期间对应的最佳资产载体;其次,与服务业消费或者即时消费品(比如游戏、比如有保质期的消费品)不同,这些具有投资属性的豪宅和茅台酒并不会因为销售而消失,在一定情况下会变成未来的潜在供给。近期,普通飞天茅台酒的市场价格调整至2500元以下,并向2400元靠拢。除了普通飞天茅台酒之外,其他品类的茅台酒经销商并不赚钱。目前,茅台市场化的经销商在普通飞天茅台酒上每瓶大致仍有500元或略多的利润,但考虑到其它茅台酒品类包括茅台冰激凌的亏损,总体盈利情况尚可。考虑到普通飞天茅台酒“去金融化”的趋势对供求关系的影响以及其团购比例的持续上行,后面需要关注如果旺季普通飞天茅台酒市场价格继续调整对行业的潜在连锁影响。
野村证券近期发布了一份90年代初日本经济泡沫破灭之后十年至二十年间各类消费品消费量变化的详细报告。报告指出,不同消费品在这段时间内的消费量变化情况大相径庭:有些品类消费量略有下降或甚至有所增长,而有些则下降了70%-80%。深入分析这些变化,差异的关键在于不同消费品类对应了不同的消费人群,从而对应了不同的人群数量变化、收入变化和生活方式、消费动机、消费场景的变化。本质上,消费品的种类并不重要,即便是同一类别的产品,如不同定位和价格的液体饮料或酒类,因为背后消费群体的不同而成为完全不同的消费品类。关键在于要穿透消费外在的形式与载体,穿透到最终消费者的属性和人设——人群数量的变化、收入变化、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的变化。例如,啤酒与液奶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消费品类,仅仅从市盈率等表面指标来分析它们的投资价值是没有意义的——前者跟中国的中青年总人口更相关,是类似于长期平均移动曲线的慢变量,而后者由于股票市场过去看的是消费升级的故事,相当程度是跟新生儿的数量及其变化速率相关(中国家庭消费首先在意的是小孩)的快变量。从这个角度看,诸如一些定位在性价比和持续涨价的女包之间的Michael Kors和Coach的“轻奢”女包,以及夹在升级的地产酒高端产品与高端酒价格中枢下移中的次高端白酒,长期看属于渐行渐远“消失的世界”。
穿透表象看本质的投资分析方法,中国如此,全球亦如此。以游轮行业为例,作为典型的可选消费和显而易见的重资产行业,如果想当然地从宏观分析的角度出发认为欧美利率持续高企行业需求下行和股票表现不佳就有失偏颇。实际上,游轮在欧美是典型的“银发经济”,许多退休老人依靠储蓄和投资的金融资产生活,他们正是美国国债收益率高企和股票ETF基金上涨的最大受益者。相比之下,星巴克一季度美国国内销售收入出现负增长也反映了当下美国的宏观环境下,城市白领面临的现实问题。相对于劳动力缺口持续紧张的中低端劳动力,城市白领工资增速相对不高,但却受高通胀影响的现实。
没有企业的时代,只有时代的企业。企业如此,行业亦如此。写到这里,想起了2021年鸿道投资公众号文章《于无声处》最后的部分:“重看电影《美国往事》的时候,不禁联想到,如果菲茨杰拉德笔下的盖茨比没有意外身亡的话后面会怎样。不管过去的禁酒令时代盖茨比有多么高能地挣大钱,多么地‘了不起’,就像《美国往事》后半部旧时代过去之后,流动的盛筵不再。要么,菲茨杰拉德和盖茨比都泯然于众人;要么,望着对岸的绿灯,‘奋力向前,却如同逆水行舟,注定要不停地退回过去’。”

从“新机制”看美国金融市场
2024年中国股票市场投资展望:中国经济走在久久为攻的大路上
美国国内政治极化与财政支出竞争性扩张的经济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