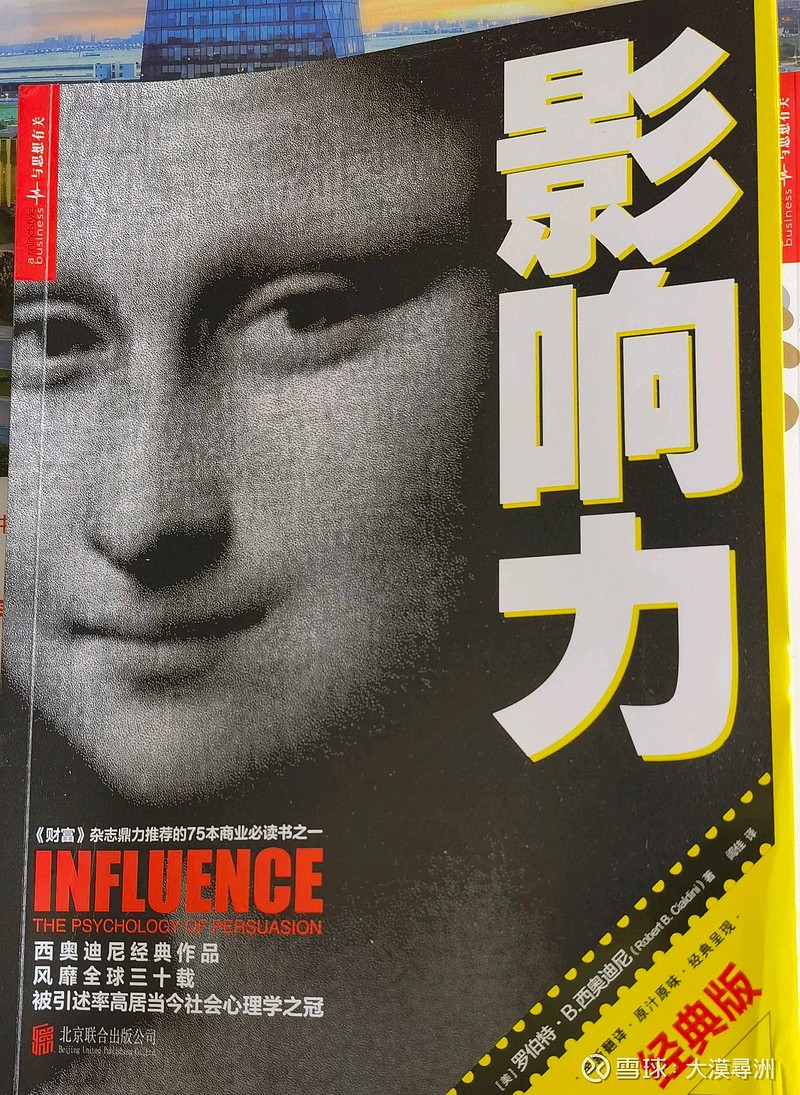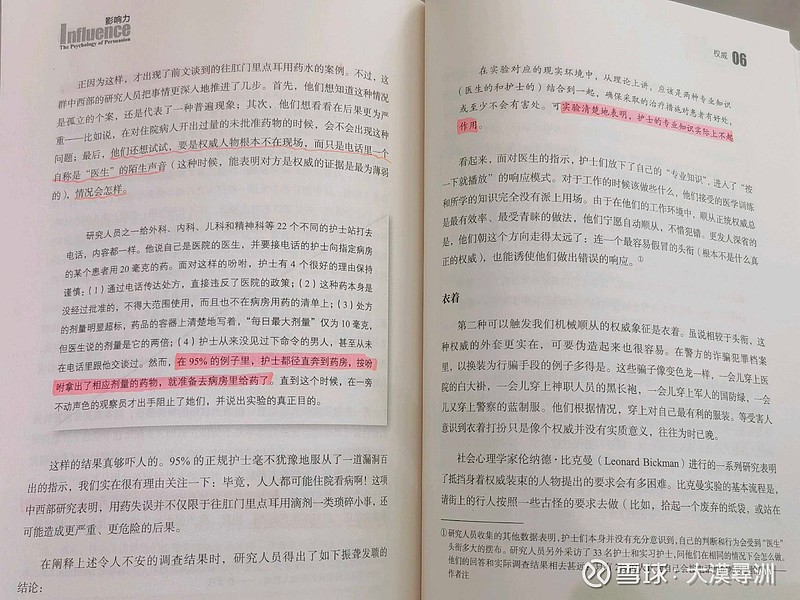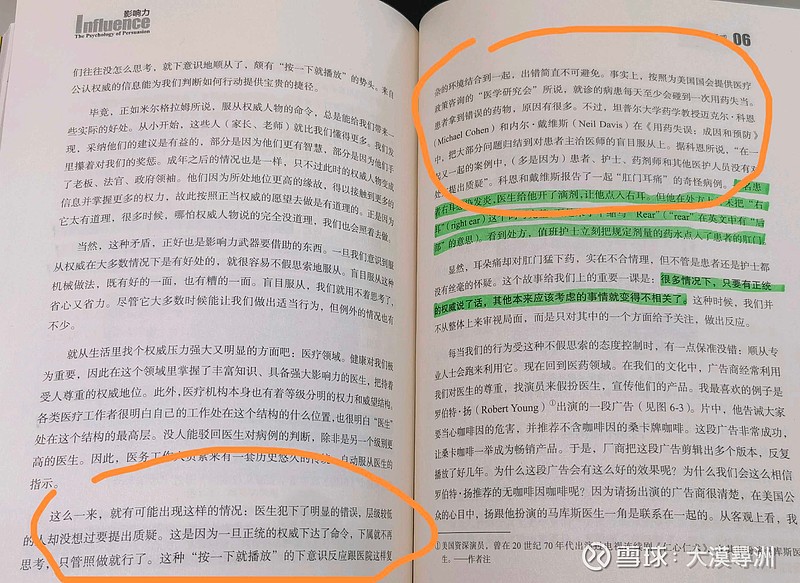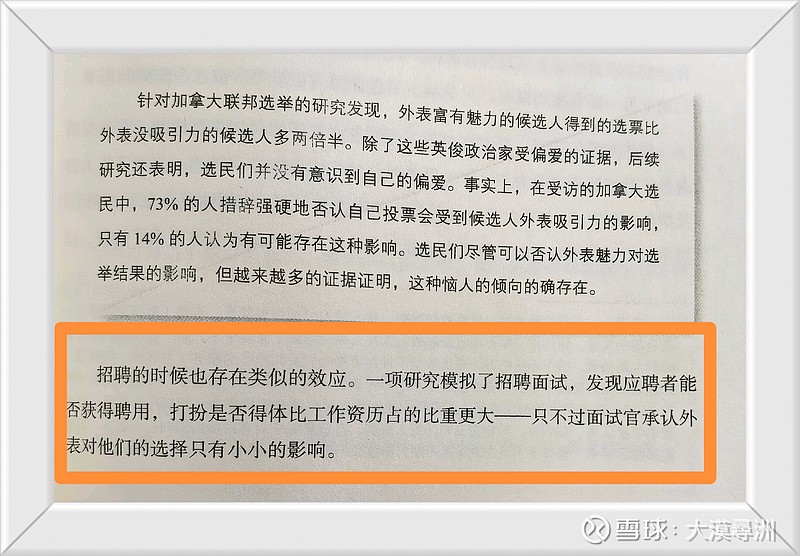文明的进步,就是人们在不假思索中可以做的事情越来越多。——英国哲学家 怀特海
人有送礼的义务、接受的义务,更有偿还的义务。——法国人类学家 马塞尔·莫斯
倘若有人对我们让了步,我们便觉得有义务也退让一步。
互惠原理通过两条途径来实现相互让步。头一条很明显:它迫使接受了对方让步的人以同样的方式回应;第二条尽管不那么明显,但更为关键:由于接受了让步的人有回报的义务,人们就乐意率先让步,从而启动有益的交换过程。
由于互惠原理决定了妥协过程,你可以把率先让步当成一种高度有效的顺从技巧来使用。这种技巧很简单,一般叫做“拒绝-后撤术”,也叫做“留面子法”。
两相结合互惠原理和知觉对比原理能产生一种令人望而生畏的强大力量。拒绝-后撤技巧便是把他们捏在一起,发挥出惊人效用的。
拒绝-后撤技巧似乎不仅刺激人们答应请求,还鼓励他们切身实践承诺,甚至叫他们自愿履行进一步的要求。
——罗伯特·B.西奥迪尼 《影响力》02 互惠
人人都有一种言行一致(同时也显得言行一致)的愿望。
要是有什么办法能省掉动脑筋这档子真正的体力活儿,人们断然不会放过它。——乔舒亚·雷诺兹爵士
只要你把一个人的自我形象设置在了你想要的位置上,那么这个人就会自然而然的遵从一整套与这一全新自我形象相一致的要求。
行为是确定一个人自身信仰、价值观和态度的主要信息源。
周围的人认为我们什么样,对我们的自我认知起着十分重要的决定作用。
每当一个人当中选择了一种立场,他便会产生维持它的动机,因为这样才能显得前后一致。
为一个承诺付出的努力越多,他对承诺者的影响也就越大。
费尽周折才得到某样东西的人,比轻轻松松就得到的人,对这件东西往往更为珍视。
只有当我们认为外界不存在强大的压力时,我们才会为自己的行为发自内心的负起责任。
这些认识对教育孩子具有重要意义。它表明,对于我们希望孩子真心相信的事情,绝不能靠贿赂或威胁让他们去做,贿赂和威胁的压力只会让孩子暂时顺从我们的愿望。倘若我们不光希望她他们暂时顺从,还希望他们相信自己做的事情是正确的,就算我们不在现场提供外部压力,他们也会继续照着我们乐于见到的方式去做,那么,我们就得做一些安排,让他们为自己的行为负起责任来。
个人承诺能建立起一套自圆其说的系统,能为最初的承诺找到新的理由。
我并不否认保持一致的重要性,但我想指出,顽固的保持一致荒谬透顶。
——罗伯特·B.西奥迪尼 《影响力》03 承诺和一致
一般来说,在我们自己不确定、情况不明或含糊不清、意外性太大的时候,我们最有可能觉得别人的行为是正确的。
尤其是在局面模糊不清的时候,人人都倾向于观察别人在做什么,这会导致一种叫做“多元无知”的有趣现象。
我们在观察与我们相似的人的行为时,社会认同原理能发挥出最大的影响力。
我们会根据他人的行为来判断自己怎么做才合适,尤其是在我们觉得这些人跟自己相似的时候。
首先,我们似乎持有这样的假设:要是很多人在做相同的事情,他们必然知道一些我们不知道的事情。尤其在我们并不确定的时候,我们很乐意对这种集体智慧投入极大的信任。其次,人群很多时候都是错的,因为群体的成员并不是根据优势信息才采取行动,而只是基于社会认同原理在做反应。
——罗伯特·B.西奥迪尼 《影响力》04社会认同
想引发不和简单的很:只要把参与者分组,让他们自发形成小圈子意识。之后,再把他们混在一起,用竞争的火焰烤上一烤。这样,不同群体之间的恨意就会像烧开了的水一样沸腾起来。
体育运动和粉丝之间的关系是非常个人化的……倘若其他条件全都一样,你铁定会支持跟自己同样性别,来自同一文化、同一地区的队伍……你想要证明自己比另一个人更优秀。你支持的一方就代表了你,它赢了,你就赢了……从这个角度来看,体育迷的狂热就变得有意义起来。我们观看比赛,并不是为了它固有的表现形式或艺术意义,我们是把自我投入了进去。这就是为什么球队主场获胜以后,粉丝们会投以那么强的崇拜和感激之情。这也是为什么球队主场失利之后,同一批粉丝会马上翻脸不认人,恨不得把球员、教练和官员生吞活剥了。
根据关联原理,倘若我们能用一些哪怕是非常表面的方式(比如我们的居住地)让自己跟成功联系起来,我们的公共形象也会显得光辉起来。
学生们穿校队队服,不是因为校队打了一场势均力敌艰难取胜的比赛,而是因为压倒性的胜利带来了不容否认的优越感。
我们会有意识的操纵我们跟输赢双方的联系,这样,在目睹这些关联的人们眼里,我们会显得更好看些。我们展示积极的联系,隐藏消极的联系,努力让旁观者觉得我们更高大,更值得喜欢。
如果我们真的会千方百计的跟成功拉关系、沾光彩,好让自己显得更好看,那么有一点可以断定:倘若我们觉得自己看起来不怎么样,那么我们就很有可能使用这一方法。每当我们的公众形象受损,我们就会产生强烈的欲望,宣扬自己跟其他成功者的关系,借此恢复自身的形象。同时,我们还会小心避免暴露自己与失败者之间的关系。
——罗伯特·B.西奥迪尼 《影响力》05 喜好
在权威的命令下,成年人几乎愿意干任何事情。——米尔格拉姆
打从出生之日起,社会就教导我们:顺从权威是正确的,违抗权威是不对的。父母的教诲,校舍里风传的小曲、故事和儿歌里,甚至我们成年后存在的法律、军事和政治制度中,无不充斥着这条信息。而所有这些“教化”,无不将服从和忠于正当规则摆到极高的地位。
我们知道判断一个行为正确与否,跟它有没有意义、有没有危害、公不公正、符不符合通常的道德标准没有关系,只要它来自更高的权威,那就是对的。
一名患者右耳感染发炎,医生给他开了滴剂,让他点入右耳,但他在处方上并未把“右耳”(right ear)这个词写完整,而是来了个缩写“Rear”(“rear”在英文中有“后部”的意思)。看到处方,值班护士立刻把规定剂量的药水点入了患者的肛门。
显然,耳朵痛却对肛门门猛下药,实在不合情理,但不管是患者还是护士,都没有丝毫的怀疑。这个故事给我们上了重要的一课是:很多情况下,只要有正统的权威说了话,其他本来应该考虑的事情就变得不相关了。
只要处在“按一下就播放”的模式,只要拿出权威的象征符号就能将我们降服了。
头衔比当事人的本质更能影响他人的行为。
我们觉得一样东西看起来大些,不一定是因为它能带给我们愉悦,而是因为它很重要。
在米尔格拉姆的研究里、中西部医院护士的研究里、警卫制服的实验里,人们都无法正确预测自己或他人面对权威的影响力会做出什么样的反应。每一次,人们都严重低估了权威的影响力。权威地位的这种性质或许可以说明把它当成顺从策略为什么会如此成功,它不仅对我们很管用,而且还超出我们的预料。
——罗伯特·B.西奥迪尼 《影响力》06 权威
商业世界的研究也发现,管理者对潜在损失比潜在收益看得更重要。就连我们的大脑似乎也是为了保护我们免遭损失而设计的:阻挠着眼于损失所做出的明智决定,要比阻挠着眼于收益的决定难得多。
倘若瑕疵把一样东西变得稀缺了,垃圾也能化身成值钱的宝贝。
保住既得利益的愿望,是心理逆反理论的核心。
想让信息变得更宝贵,不一定非要封杀它,只要把它弄成稀缺信息就行了。根据稀缺原理,要是我们觉得没法从别处获取某条信息,我们就会认为它更具说服力。
两位心理学家迪莫西·布罗克和霍华德·弗洛姆金提出一套对说服力进行“商品分析”的理论,它们的理论的中心论点就是:“独家信息最能说服人”。
新出现的稀缺更使人觉得迫切的适应范围,远远不止局限于饼干试验。举例来说,社会科学家已经确定,这种稀缺是造成国家政治动荡和暴乱的主要原因。这一观点最重要的支持者詹姆斯·戴维斯曾指出,一个国家在经济和社会条件改善后,要是在短期内出现剧烈逆转,最有可能爆发革命。
自由这种东西,给一点又拿走,比完全不给更危险。
跟一贯的稀缺比起来,一种本来有后来没有了的东西,会让人更想要。
管教前后不一的父母,最容易教出反叛心强的孩子。
较之供应充足的饼干,稀缺的饼干得到了较高的评价,从充足转为稀缺的饼干,所得评价更高。
我们不光在物品稀缺时更想要它,而且碰上有人竞争时最想要。
参与竞争稀缺资源的感觉,有着强大的刺激性。
渴望拥有一件众人争抢的东西,几乎是出于本能的身体反应。
在碰到稀缺资源加竞争的魔鬼组合时,务必小心谨慎。
喜悦并非来自对稀缺商品的体验,而是来自对它的占有。
稀缺的东西并不因为难以弄到手,就变得更好吃、更好听、更好看、更好用了。
——罗伯特·B.西奥迪尼 《影响力》07 稀缺